首個雙手控制腦機接口:開顱手術10小時植入6個電極,癱瘓人士用意念吃蛋糕
本文轉自雷鋒網,如需轉載請至雷鋒網官網申請授權。
有這樣一位名為 Buz Chmielewski 的男子,曾在一次出海沖浪時不幸遭遇意外,四肢癱瘓。從正值十幾歲的大好年華到此后的 30 余年里,Buz Chmielewski 的手臂幾乎不能做出任何活動。
雖然再也無法回到少年時的那般健康有活力,但他還是鼓起勇氣接受了一組來自美國著名私立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應用物理實驗室研究團隊的實驗,挑戰常人眼中的不可能。
幸運的是,實驗很成功!
Buz Chmielewski 借助科技的力量,用意識同時控制了兩條機械臂,這在醫學上還是首次。
首先,他控制左機械臂拿刀、右機械臂拿叉,切開盤子里的蛋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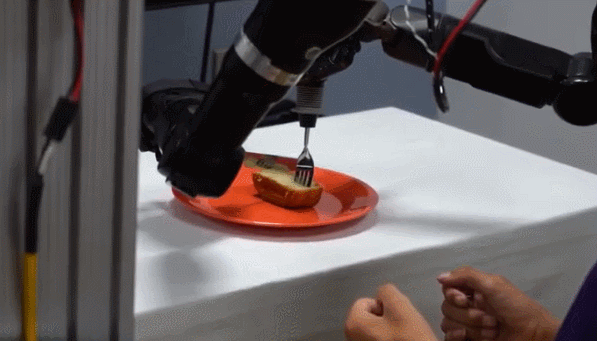
接著,其中一條機械臂緩慢移動,將蛋糕送到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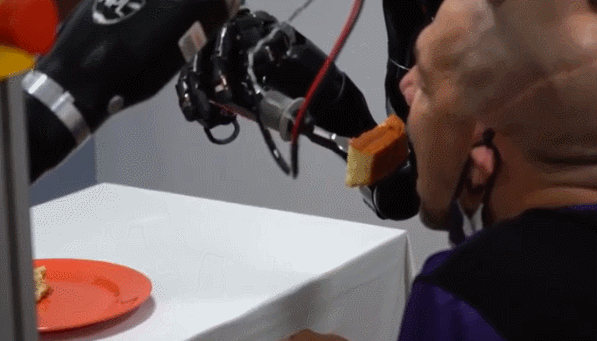
其實,研究團隊用在他身上的正是大眾既耳熟能詳又表示擔憂的一項技術——「侵入式腦機接口」。
10 小時手術植入 6 個電極
這項實驗被稱為「雙邊腦機接口植入實驗」。
早在 2006 年,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發起了與這一實驗相關的一個項目,希望研究團隊能夠盡快改進義肢(上肢)的技術,為患者操作義肢提供新的思路方法——其最初的設想是創造一個具有類似人類能力的神經集成義肢(上肢),隨后慢慢衍生出了模塊化假肢(MPL),集成了諸如應用于指尖的壓力和加速度傳感器。
2019 年 1 月,在長達 10 個小時的手術中,外科醫生將 6 個電極植入了 Buz Chmielewski 的大腦,旨在改善其雙手對外界的感知,實現傳說中的意念控制。
具體來講,Buz Chmielewski 的大腦兩側(控制運動和觸覺的區域)植入了皮質內微電極陣列傳感器。手術中團隊還用到了一種首創的方法,通過實時繪制大腦活動圖來確定放置電極的最佳位置。
手術后,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應用物理實驗室兩個團隊開始了近 2 年的聯合研究,終于達到了上述這一重要的里程碑。
如下圖所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工程師 Francesco Tenore 博士站在 Buz Chmielewski 一側,密切關注著他對兩條機械臂的意識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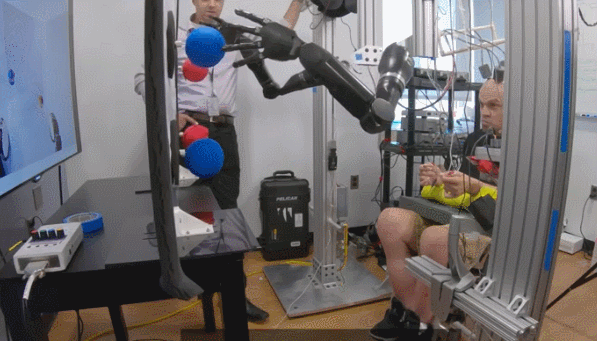
正如研究團隊成員、醫學博士、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理療與康復主任、教授 Pablo Celnik 所說:
這種類型的研究,我們常稱其為腦機接口(BCI),目前絕大多數嘗試都集中在通過控制大腦的一側實現單機械臂的控制。因此,通過植入電極從大腦兩側檢測信號,控制兩條機械臂執行基本的日常活動,可以說是實現更為復雜的任務的重要一步。
對此,研究團隊成員、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理療與康復助理教授、Gabriela Cantarero 博士補充道:
借助腦機接口同時控制兩條機械臂是一項特別的挑戰,因為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求和,不是說只要在大腦中算出左臂的動作+右臂的動作就行。在這里,可能 1+1 并不等于 2,1 + 1 = 3.8。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突破性實驗其實是腦機接口+機器人+人工智能的共同成就——在患者體外的硬件部分,研究人員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實現了機械臂控制的部分自動化。如果說 Buz Chmielewski 的努力在于通過意識控制保證細節(如:蛋糕的準確位置、蛋糕切好后的具體大小),那么機器人部分的工作則是為了讓這些基本動作更易達成。
實際上,研究團隊一直在探索利用神經信號實現系統的“實時”控制。為了檢測效果,還有三位參與者加入了神經控制研究,最終三位參與者都成功實現了單機械臂神經控制。
就未來而言,該團隊還在研究通過神經刺激同時為患者雙手提供感覺反饋的方法。Francesco Tenore 博士表示:
下一步的工作包括:增加患者日常活動的數量和類型,從而證明這種形式的人機合作是可靠的,從而為用戶提供額外的感官反饋任務。這也就意味著,患者不必完全依靠視覺來判斷是否成功,就像普通人系鞋帶時不用看也能感覺到自己的動作,把鞋帶系好。
終于,利用大腦植入物,四肢癱瘓的患者能夠用意識同時控制兩條假肢了,這無疑對于脊髓高度損傷和神經肌肉疾病患者的能力恢復有著重要意義。
腦機革命:侵入 or 非侵入?
近年來,腦機接口領域的重大突破逐漸多了起來。
2020 年 1 月 16 日,浙江大學正式宣布了“雙腦計劃”的科研成果,植入電極的志愿者可利用大腦運動皮層信號精準控制外部機械臂,實現三維空間的運動。
2020 年 4 月 23 日,《細胞》(Cell)雜志刊登了一篇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重磅研究論文,介紹了一個通過腦機接口系統來恢復嚴重脊髓損傷的患者手部觸覺和運動能力的案例,該案例中觸覺準確率已達到了 90%。
在腦機接口領域,最出圈的公司莫過于硅谷鋼鐵俠馬斯克的 Neurali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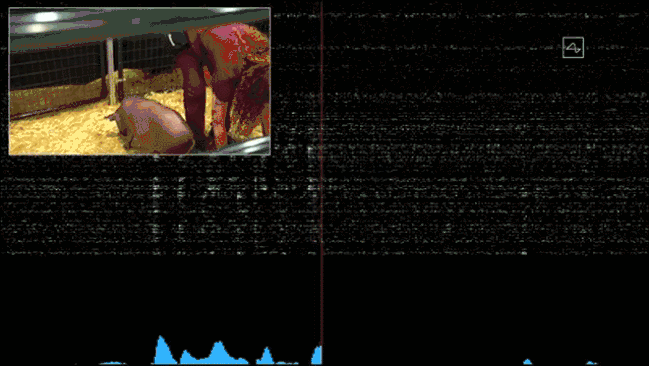
北京時間 2020 年 8 月 29 日上午 6:40,Neuralink 舉行發布會,展示了最新的可穿戴設備 LINK V0.9 和手術機器人,并通過現場的三只小豬和實時神經元活動演示,展示了 Neuralink 腦機接口技術的實際應用過程。
即便馬斯克在電動車、腦機接口、上火星等領域都十分激進,但在萬眾期待的 Neuralink 發布會上,馬斯克請來現場展示的仍然不是人類,腦機接口技術的難度由此可見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三例均屬于「侵入式腦機接口」,即必須將電極植入到人腦中,而與之對應的「非侵入式腦機接口」則是僅將電極放置在人的頭皮上,進行信號采集。
談起后者,繞不開一位中國企業家——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
在腦機接口方面,陳天橋更為注重的是「非侵入式腦機接口」。2020 年 10 月,TCCI(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的首個「腦科學前沿實驗室」在上海落成,中美腦科學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也一并展示,其中諸如用嗅覺控制夢境的腦科學領域研究令眾人眼前一亮。
實際上,目前國內外已有眾多企業也開始了非侵入式的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算法、體外電極貼、手機 APP 檢測睡眠質量、解決睡眠問題的嘗試已然存在。
不論哪種方式會更先被大眾認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腦機接口技術發展已是大勢所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