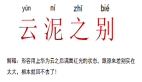這幾個月來,微軟、谷歌、甲骨文、蘋果等一眾科技巨頭紛紛裁員。日前,Meta成為又一家啟動大規(guī)模裁員的科技公司。在這波裁員潮中,Meta的操作引起了諸多爭議。爭議焦點在于它將裁員的決定權(quán)“交”給了算法。
被算法“炒魷魚”的合同工
據(jù)悉,Meta此次的裁員對象是60名合同工。這些合同工是Meta經(jīng)由埃森哲奧斯汀分公司聘用的,主要工作是幫助Meta審核其各社交平臺的帖子,識別并標記暴力色情等違規(guī)圖片,監(jiān)督商標侵權(quán)等問題。雖然屬于外聘,但他們也能享受Meta正式工的大部分福利。
但在近期,合同工發(fā)現(xiàn)Meta不僅在陸續(xù)取消他們的各種福利和補貼,對他們的績效管理也漸趨嚴苛。據(jù)有關(guān)人士爆料,只要合同工的電腦有超過8分鐘的不活躍時間就將被自動判定為在“休息”,進而被計入到每天規(guī)定的休息時間之內(nèi)。如果休息時間超額,就會被系統(tǒng)自動警告并列入績效改進計劃。
而這種激進的做法成為了裁員的序曲。很快,一批合同工收到了裁員通知。他們被告知將于9月2日解約,而薪酬結(jié)算至10月3日,即公司僅為此多付一個月的工資。
至于裁員的原因,Meta方面語焉不詳,只表示裁員對象是“隨機”選中的。而埃森哲方面則透露,是算法“提供”的名單。
此事一出,不少人質(zhì)疑算法裁員的做法過于簡單粗暴,并不具備信服力。也有人戲稱,以后機器將“掌握”公司的生殺大權(quán),高管們可以躺平掙錢了。
來自機器的冰冷“審判”
雖然Meta裁員事件中只涉及合同工,但打工人普遍可以感受到某種危機的逼近——那種來自于機器的冰冷“審視”和“審判”。
近幾年,尤其是疫情迫使遠程工作成為一種常態(tài)后,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將算法作為考核員工、評定績效,甚至決定裁員與否的重要工具。算法隱于幕后,承擔起“監(jiān)工”和“審判者”的作用。
去年8月,俄羅斯一家在線支付服務(wù)公司Xsolla使用算法解雇了包括工程師在內(nèi)的150人。為保證疫情期間線上辦公的效率,Xsolla從去年年初啟動了一套全新的由AI驅(qū)動的績效評價系統(tǒng),讓機器以百分制自動給員工打分。
而根據(jù)Xsolla的說法,算法裁員的判定標準主要來自于員工的“數(shù)字足跡(Digital
Footprint)”。所謂數(shù)字足跡,就是員工在線工作時的種種執(zhí)行動作,包括是否及時閱讀并回復(fù)郵件,是否在內(nèi)部討論中踴躍發(fā)言,是否能積極協(xié)作共同編輯文檔,是否準時上線參與遠程會議等等。
由于Xsolla的業(yè)務(wù)發(fā)展在去年下半年嚴重受挫,不得不以裁員的方式緩解經(jīng)營壓力,這套由AI執(zhí)行的績效評價系統(tǒng)就此發(fā)揮了作用。其CEO Aleksandr Agapitov在發(fā)送給被裁員工的郵件中措辭強硬地表示,AI追蹤了他們線上辦公的各類履跡,發(fā)現(xiàn)他們沒有時刻保持工作狀態(tài),認定他們?yōu)椤安痪礃I(yè)”或“效率低下”,所以Xsolla與他們并不適配。
Xsolla不是第一家采用算法裁員的公司,但其在這一過程中表現(xiàn)出的立場卻值得深思:靠數(shù)字足跡判斷員工合格是否合理?未來打工人是否必須按照AI的好惡來行動?
申訴無門的打工者們
事實證明,當機器的“審判”成為唯一標尺,人的聲音終將被湮沒。
亞馬遜很早就開始構(gòu)建一整套人工智能效率監(jiān)測及評估系統(tǒng),其Flex“零工司機”物流配送項目也由算法所掌控。算法會監(jiān)督司機們的日常工作及路線,比如是否在規(guī)定時間完成了配送、是否將包裹放到了指定位置,再綜合司機們的表現(xiàn)將他們分成不同評級,不合格的員工將直接收到系統(tǒng)自動發(fā)送的解雇郵件。
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多司機都遇到了不可控的運送延遲問題。比如,亞馬遜系統(tǒng)會在深更半夜給司機派發(fā)帶密碼的公寓大樓的配送工作,結(jié)果是既找不到人開門,用戶電話也無人接聽;再比如,亞馬遜系統(tǒng)要求將包裹送到指定儲物柜,但司機卻發(fā)現(xiàn)儲物柜故障打不開,等撥通服務(wù)電話后又被通知將包裹退回分揀中心。
盡管這些意外都是由于算法失誤導(dǎo)致的,但結(jié)果是很多司機因此評分下降,甚至被辭退。更令人無奈的是,在被算法錯誤判定責任后,司機們基本申訴無門,因為申訴后,面對的也是機器人的自動回復(fù)。申訴,自動回復(fù),再申訴,繼續(xù)自動回復(fù),循環(huán)往復(fù),無有出期。
“當你對抗的是機器,就不可能贏,所以甚至不想去嘗試。”一名被解雇的司機感慨道。
整體上看,機器能比人類更快、更準確地做出決策,降低人力成本,所以Flex項目對于亞馬遜來說是成功的。它填補了巨大的司機缺口,幫亞馬遜完成了最后一公里運送。但這種運轉(zhuǎn)機制也讓眾多零工司機成為了“消耗品”,哪怕因算法受到不公,也只能和機器申訴,和機器對抗,最后還要被機器踢皮球。
別讓AI取代“人性”
對企業(yè)來說,將日常管理、監(jiān)督、考核等流程通過算法實施,無論實際執(zhí)行效果如何,主要還是為了降本增效。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yè)都開始引入復(fù)雜的OA算法管理系統(tǒng),但有時候,這種趨勢也存在某種危險的傾向。
首當其沖的就是其無孔不入的屬性。畫面識別工作狀態(tài),讓員工心率、呼吸、疲勞度等數(shù)據(jù)一覽無余;電梯攝像頭與OA系統(tǒng)相連,還配置錄音設(shè)備,讓員工開個玩笑都要謹小慎微;更有甚者,計算員工去衛(wèi)生間的時長,并與績效掛鉤。如此種種,“管理就是數(shù)字”變成了真實而殘酷的現(xiàn)實。
算法裁員也是這一不斷升級的管理手段下的產(chǎn)物。但稍加思考,這一手段背后其實隱藏著種種“不可解”:
其一,算法的“黑箱性”讓人無法信服。這也是人工智能長期面臨的AI模型的透明度和可解釋性問題。算法判定裁員的標準,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可能連開發(fā)人員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其具體細節(jié)。不解決這一問題,也就無法讓人信服,還會帶來算法歧視、算法安全等方面的質(zhì)疑。
其二,算法裁員的“合法性”讓人存疑。算法開除的決定是否符合勞動保護條例?算法作為裁員的唯一依據(jù),還是算法作為裁員的部分參考,兩者顯然存在明顯區(qū)別。如果只是試圖讓算法“背鍋”,拒絕人性化溝通,算法裁員無疑就成為了公開的笑柄,引起的必是員工的逆反和公眾的群嘲。
其三,算法裁員在某種程度上抹殺了員工的“個性”。算法裁員機制下,每個員工都成為了面目模糊的數(shù)字孿生體,被不可避免地異化了。他們的工作過程、工作成果被系統(tǒng)量化,記錄成一個個數(shù)字,本該更具人性化關(guān)懷的裁員溝通也因算法的介入變得極度冰冷。
當AI深入到企業(yè)經(jīng)營的關(guān)鍵領(lǐng)域當中,有個問題越發(fā)突出:機器是無法完全理解人的,人的行為和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被量化,要警惕AI取代/削弱人性。
工作時間去公司樓下買個面包,不意味著工作不負責;與同事交談開個玩笑,也不代表辦公不認真;攝像頭前沒有時刻精神飽滿,不代表工作成果不完美;在衛(wèi)生間多待幾秒,更不能和磨洋工劃上等號。時刻處于“監(jiān)視”之下,那是“犯人”,不是“員工”。
算法再強、AI再智能,也無法突破0和1的字符世界,洞察人性的幽深,明辨世相的曲直。人機共生的和弦里,技術(shù)的力量音符上必然要加持人性的輝光。
參考鏈接:
http://www.sycaijing.com/news/details?id=124188&type=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3877376413964405
https://www.elecfans.com/d/1706076.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8827286904015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