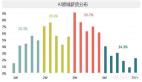三人「圍桌」腦科學VS人工智能,相互博弈中如何突圍?
IDG資本投資人,聯合神經科學大咖與前沿科技企業家,來了一場高強度、高信息密度對話,全程高能,術語名詞飆到飛起。
從1943年基于神經元提出的機器學習早期數學模型,到人工智能巨頭 Hinton提出可能成為CNN替代品的「膠囊網絡」,再到近日斯坦福團隊提出「意念手寫」的腦機接口……幾十年來,神經科學在人工智能的研究歷程中都舉足輕重。在AI的發展中,研究人員一直試圖模仿大腦的功能,用大腦的工作機理構建神經科學與人工智能之間的橋梁。
如果人工智能代表了當今最前沿的技術,那么作為支撐其發展的基礎科學——腦科學,就是最初的研究動力。從基礎科學層面來看,腦科學運用生命科學、物理科學、信息科學等綜合手段,從分子、細胞、心理、計算網絡等多個層面,對神經系統進行研究;而從前沿科技層面來看,以腦機接口、類腦芯片為代表的交叉學科的發展已將腦科學推向了時代的浪尖。
可以說,如果沒有神經科學大的理論突破,沒有對智能生物原本的認識,人工智能的「智能」可能就是一個黑箱。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智能」,它與腦科學的關聯又有幾何?
近日,IDG資本合伙人牛奎光,商湯科技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徐立,清華-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魯白教授圍繞「人腦VS智能」展開了熱烈討論。三人從科研、資本、企業等不同角度探討了當下推動基礎科學研究與技術產業化加速融合的路徑和建議。

從左向右依次為:IDG資本合伙人牛奎光,國際著名神經學家魯白教授,商湯科技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徐立
腦科學VS人工智能:相互促進,相互博弈
「深度學習算法,本質上是在向人腦的生物學的組織方式進行一些學習,雖然不是全部,它其實還是在向生物學的方式學習,其實從生物的角度上來講,可能也可以為IT進行很多的支撐。」在對話開始不久,IDG資本合伙人牛奎光就對人工智能與基礎生物學的關系進行了一個梳理。
基礎科學之于前沿科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腦機接口、類腦計算機等AI應用異軍突起,腦科學的深入研究便是其背后的推動力量。可以說腦科學提供了很多新思路來幫助計算機進行類腦計算或者開發新的算法。那么,腦科學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其與人工智能的關聯又體現在哪?
首先,治療腦疾病是其最重要的要解決的方向。腦機接口,就像打開了人和機器之間進行交流的大門,讓四肢癱瘓的人使用大腦來控制仿生假肢,讓語言障礙人士說話。例如,去年備受矚目的馬斯克「三只小豬」實驗。 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展示了通過將腦機接口設備植入小豬大腦,實時讀取其腦部活動信號的技術。
不僅如此,未來人類很有可能利用腦機接口來對抗癲癇、重度抑郁癥、自閉癥、阿爾茲海默癥、帕金森綜合癥等目前難解的神經疾病。
其次,提升人類的學習速率。人機交互可以提升人腦的反應時間。比如你開車來不及轉彎的時候,一個一閃即逝的想法,機器就能幫助你迅速操作方向盤,秒摁急剎車。
「腦科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魯白認為,「感知、運動、記憶、情緒以及認知。其中感知與運動是相對比較成熟的兩個領域。它們把腦的電信號轉換成運動信號,深度學習算法也是類似的處理信號。」
在魯白看來,基于過去二十年里科學界對神經科學的深入研究,目前感知、運動已相對成熟;而記憶則是目前進展最快的領域,其機制正有望達到一個新的突破。
但如果說感知與運動是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的大融合;那么剩下的三個方面,就是二者互相博弈的地方。因為情感和情緒是計算機所不具備的,其神經環路、神經遞質、分子、基因等都已研究得比較透徹。
魯白提到的「情感和情緒」正是強人工智能(AGI)的體現。認知,是人類最想知道但進展并不顯著的領域。而AGI就代表了「能理解、會思考」,有類似人類認知智能的表現。
得益于深度學習的快速發展,機器智能的感知能力已得到大幅提升。在過去十年中,感知智能、認知智能之間的關系已經廣泛被行業所接受。世界上最頂級的研究院微軟、谷歌、IBM和中國下一代人工智能的整體規劃都把感知智能和認知智能作為將來研發的主要目標的突破方向。
要知道,人腦本身是一臺驚人的計算機!它能夠以高達每秒6×10^16位的速度傳遞大量的信息。因此,腦科學一直被視為人類理解自然界現象和人類本身的「終極疆域」。無論是會敲代碼、寫論文的GPT-3,還是可將腦中筆跡轉為屏幕字句的「意念腦機接口」。
可以說,大腦都是AGI強大且唯一的「博弈對象」。
全球掀起科研范式新浪潮,中國如何突圍?
「去年看到這個事情時,我很震驚。」牛奎光提到了這樣一個案例,「人工智能居然能夠幫助去做蛋白質展開,這個是非常震驚的一個事情,以前以為是單方向的引領,后來發現可以雙向輔助。」
當時,DeepMind的深度學習算法AlphaFold,利用DNA序列成功預測蛋白質折疊。在此之前,這個問題在生物圈已被研究50年之久。這一「諾獎級」里程碑被Nature雜志評價為:可能改變一切。
「這在科研的范式上,形成一個重大的改變,大多數科學家還沒意識到這個問題,少數走得比較前沿的科學家,卻已經開始意識到了。」魯白補充道。
科研范式的變革,需要相應改變科研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及組織方式。從古至今,許多科學大家都對「范式」提出了自己的準則:亞里士多德賦予其演繹,培根講求歸納,牛頓善用實驗……那么今天呢?
可能不需要技術,也不需要經驗,甚至不需要假說,基于大量的數據,我們科研范式在悄然改變。
「當中有另外一波,就是從腦科學當中借鑒來的。」對此,作為人工智能領域領先的從業者,商湯科技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徐立,從計算機的角度補充道,「我們講的深度學習,其實是一個超大數據歸納的方法,可以看成原來那套體系是一個演繹的推演到極致,你可以想象得出來,技術推演的邊界。大數據是一個歸納的,到了一個更大的極致。」
「AlphaFold2有了大量的數據積累,只需要知道序列就可以對蛋白結構進行解析,這在科研范式上形成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人類有兩萬多個基因,對應兩萬多個蛋白,通過AlphaFold2這樣的人工智能系統可能會很快地解析完,這樣就可以知道蛋白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可以基于結構尋找小分子藥物靶點,自然也可以應用于腦疾病的藥物研發上來。」魯白從科學的角度解釋說。
那么,這依舊是一個「西式」的范式嗎?在徐立看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會有一個更好的發展機遇。并且在這種新興的突破式范式下,中國早已有了一個天然的支持原始創新的新土壤。
腦科學作為打破傳統科研范式的先發地之一,早已形成了支持創新的沃土。除了世界各國先后啟動的腦科學計劃、政府的大力投入外,以IDG創始人及董事長麥戈文先生及IDG資本為代表的民間捐助也成為了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之際,麥戈文先生就與清華大學簽署協議,成立了清華大學-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同年還相繼捐贈了北大、北師大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2021年4月22日,IDG資本與清華大學宣布繼續攜手探索和助力中國腦科學的基礎研究和未來發展。
2021年,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希勤與IDG資本創始董事長熊曉鴿在「IDG資本-清華腦科學發展基金捐贈儀式」上合影
「凝聚共識是一個很重要的事。」魯白介紹說,作為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的他,對中國腦科學發展有著清晰的見證,「清華腦科學的崛起,跟麥戈文和IDG資本是非常有淵源的,整個腦科學把它叫做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院。」
另外,腦科學作為一項長線的投資,不僅吸引著資本與科研界的眼光,企業界也對此重視頗深。例如,徐立就以理事身份參與到了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院的相關工作中。
突破「逃逸速度」的企業,能在創新的宇宙中暢游
牛奎光回憶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準確地說,是2014年——人工智能尚未產業化的時候。「我跟徐立聊,如果人工智能產業化之后競爭激烈了怎么辦,他給我打個了比方,如果我們要做一個貓腦子的智力水平系統,你創業可以做兩件事,第一訓練貓去抓耗子,做應用;第二努力把貓的腦子提高到猴子腦子的智力水平。其他人都在做第一個,商湯第一個也要做,但更重要的是做第二個。」
「因為如果要做的事情是摘果子,我們現在只有一只貓的腦子,只能抓耗子,我們就必須把它升級成為一只猴子的腦子,這就是我們想做的底層延伸。」徐立說。
秉著這樣的理念,徐立帶領團隊用神經科學的機理來做人工智能。「真正能夠帶來一個非對稱的優勢的核心能力,是在于非連續的跳躍。真正的突破還是在于,你需要把它們做升級,才能夠達到生產力,剛才是講工業的紅線。」
在徐立看來,「原創的投入力度要足夠大,如果真的以原創這件事情作為核心競爭力的時候,你投入的密度要足夠大,就是逃逸速度。你在地球上跳總是有吸引力,但是你速度達到了宇宙速度,你就感覺沒有引力了,所以單點投入的密度要大,而且要堅決。」
其實創新的真正意義,在生物學中就有跡可循。生物學的選擇方面最核心的觀點是,種群之間的競爭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種群內部的競爭。類比到企業也是一樣的,不同企業之間有競爭,企業內部不同部門之間也在競爭有限的資源。生物學競爭是自然淘汰、適者生存;企業也是市場淘汰、適者生存。
牛奎光說,「創新基本都是打破共識的,科學研究也是這樣。打破的舊的共識越大,同時會形成新的共識,因為只有形成新的共識這個企業才會有價值,形成新的共識越大這個企業的價值就會越大,當然也就會越難。」
「只有做跟大家不一樣的東西,才能夠在這個地方上找到行業的契機,才會有資源差,才會形成壁壘。創新就是在形成不平等的資源差,然后形成生產力的大突破和變現。」作為一家「適者生存」的公司的CEO,徐立也這樣認為。
但是必須承認的是,創新是無法由企業或研究機構獨立完成,它需要有一個包括資本在內的完整生態網絡支撐。
企業是創新的主體,高校能為創新提供原動力,而資本則負責尋找打破共識的人。當三者聯動起來,就會產生非常積極的效應。
那么,目前中國整個市場環境是否已經達到了支持原始創新研究的階段呢?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企業本身走的是用原創產生競爭力的道路。其次,市場環境允許基礎研究做無用的研究,因為從創新的角度來說,這才是在探索我們認知的邊界,制造「逃逸速度」。
根據數據統計,從人工智能崛起的近五年來看,伴隨這一現象的,還有腦科學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這不僅是科研界、投資界以及企業界的三方努力,更是從國內到全球對腦科學重要性的一個空前共識。「逃逸速度」已經蓄勢待發,突破了創新最后的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