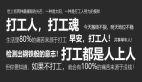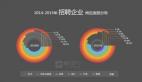35歲互聯網“打工人”生存調查:轉行、創業、出國
門外的人想進去,門內的人不想出來。
用這句話形容互聯網行業“打工人”,似乎非常準確。根據 10 月 28 日澤平宏觀發布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報告》,2019 年求職人才最多的行業是 IT、通信、電子、互聯網行業;而 2020 年就業季,脈脈數據研究院最新的報告顯示,IT 互聯網行業是應屆畢業生最熱門行業選擇。
但在一批又一批“后備軍”加入互聯網行業之后,一群 35 歲左右的互聯網“老兵”們,卻用“中年危機”形容自己的職業生涯。
汪程(化名)今年即將滿 35 歲,從事互聯網行業 12 年,看著一批又一批年輕人進入公司,他感受到了焦慮,“年輕人又能加班又能扛,薪資也不是特別高,公司肯定都愿意招年輕的新員工,性價比高。”
面對所在的團隊基本上都為 25 歲的年輕人,汪程說起這句話有自嘲,但也并非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價值。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不少互聯網“老兵”們開始兼職、培訓和做自媒體,尋找“新賽道”。
從事互聯網人力資源培訓的尚德機構旗下人力資源資深分析師李強,接受 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面對“中年危機”,互聯網人應該保持持續學習,不管是走管理路線還是專業路線。此外還可以通過寫博客,寫書,增加職業社交等,擴展自己的職業前景。
“中年危機”的互聯網人
35 歲,本是眾多職場人士漸漸走向成熟的年齡,但對于互聯網人來說,35 歲似乎是職場生涯的分水嶺,因為有太多年輕人想進入這一高薪的行業,尤其是互聯網大企業。
脈脈數據研究院最新的報告顯示,互聯網企業人才吸引力取決于“未來預期+企業穩定性+工作時長+員工評價+通勤時長”這五個評估要素。
一位應屆畢業生對 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他的目標是進入互聯網大廠,因為互聯網企業的薪資層次分明,在互聯網大廠,即使剛剛畢業薪酬也上萬元,而如果其他企業,則是 7000-8000 元甚至 4000-5000 元。
但這些年輕的“后備軍”的“躍躍欲試”,難免讓互聯網“老人”們焦慮,盡管他們大多不過 35 歲上下。
2019 年,58 同城招聘研究院曾發布程序員行業大數據報告顯示,46.88% 的程序員年齡集中在 21-25 歲,25 歲以下(包括 25 歲)的從業人員占比達 62.84%,而 41 歲以上的從業人員占比只有 1.99%。在工作年限方面,工作1-3 年從業者占比最高,達到 29.37%。工作 10 年以上的從業者占比最低,只有 6.83%。
汪程就是罕有的工作超過 10 年的互聯網程序員,盡管他目前已經逐漸過渡到帶領團隊。
“我目前帶領團隊完成一些系統的業務,類似于 OTO 系統等。團隊成員年齡大概在 25 歲左右,他們一般工作兩三年跳槽,有些甚至干一年就跳槽,公司流動率比較高。”他告訴 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但汪程并沒有這一打算,他指出一般工作四五年以后,薪資變得比較平穩,漲幅不是特別大,所以說工作時間越久,跳槽反而不頻繁。
和汪程相比,柳鎮(化名)已經 39 歲了,可卻是“半路出家”,3 年前才跳槽到互聯網行業當工程師,難免更焦慮。
“我們團隊平均年齡不到 30 歲,我的工作職位處于一線,還沒有工作經驗,得跟剛畢業的年輕人競爭工作崗位。”柳鎮在制造業呆了了十多年,之后轉行到互聯網做圖像測試方面的工作。他所在的公司屬于外包公司,客戶有一個大型芯片項目,他負責其中一個模組 ISP 的性能測試。
他表示,要賺錢養家,工作機會又少,必須“熬下去”。“我覺得干一行不能輕易地放棄,目標是做到5-6 年。”
而今年 42 歲的趙軍(化名),曾“熬”得非常辛苦,是典型的“996 上班族”,無法做到兼顧家庭與工作。但在 35 歲時,他辭掉國內工作,來到澳大利亞發展,一年能有 20 天的年假,“談不上逃離,只是換一種生活方法”。
趙軍在國內的最后一份工作,團隊成員大概 30 歲出頭。他對互聯網人的“中年危機”感受更為深刻,認為所謂的中年危機,是因為互聯網人工作了十幾年后,待遇得到相應提高,但產出仍然和大學畢業時差不多,從公司效益的角度來講,肯定是需要更廉價的勞動力。
一些城市的生存競爭壓力更高,這時候不少互聯網人會選擇到其他城市去工作,比如一些深圳的互聯網人有時候會選擇來廣州。-甘俊攝
“當前國內互聯網行業仍然處于野蠻生長階段,程序員行業非常火爆,供需比較失衡,中年危機不可避免。因為高校供應的互聯網人太多了,年紀大了以后被淘汰這個問題難以完全緩解,我個人認為,最近一二十年都不會有很好的改變。”趙軍說。
根據麥可思發布的 2020 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2019 屆本科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 5440 元,其中,計算機類、電子信息類、自動化類等本科專業畢業生薪資較高,2019 屆平均月收入分別為 6858 元、6145 元、5899 元。
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盤點后發現,在最近 10 年,互聯網行業一直保持在大學生就業排行榜薪酬的前五位,這也說明為何很多畢業生希望進入互聯網行業,這一行業 35 歲“打工人”不斷受到沖擊的局面,近期很難改變。
上述人力資源資深分析師李強指出,互聯網行業的工作節奏比較快,相較于其他行業危機感會顯得更加明顯。35 歲這個年齡層次的人,更多是期望家庭與事業的平衡,不能再像剛畢業一樣,可以把 100% 的精力放在工作上,而互聯網行業是一個公認比較燒腦的職業,如果 35 歲還在一線,的確會比較容易身心疲憊。
如何應對“中年危機”?
互聯網人“中年危機”難以避免,要如何應對呢?
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采訪后發現,出國、兼職、創業等,都是 35 歲左右互聯網人的選擇,另外一個重要的選項就是加深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汪程認為,可以通過提升個人價值來緩解中年危機感,在工作中積累經驗,平時多梳理和沉淀技術和業務知識點,“要提升在項目團隊里的重要性,比如公司的某一塊業務除了你,沒有其他人能夠比你更懂。”
趙軍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表示,緩解中年危機要提升自身能力,與時俱進,同時提升能力要將學習與工作結合起來,“程序員不光是一種重復性的勞動,雖然很多情況下都是用現成的技術來解決新的問題,但肯定會查很多的資料,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深度了解與工作相關的內容。”
李強指出,互聯網人應該保持持續學習,不管是走管理路線還是專業路線,在互聯網領域不要脫離技術,互聯網的技術更新迭代太快,幾乎半年更新一次,如果脫離技術太遠,可能很快被市場淘汰。
但趙軍認為,不管如何學習,中年危機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因為不可能所有人年紀大了都能留在崗位上,肯定會慢慢轉行,或者選擇出國。他是一名嵌入式高級軟件工程師,從事國際領先的火警系統開發,十幾年間大概換過 5 份工作。他目前在澳大利亞工作,認為澳大利亞對互聯網人年齡比較寬容,團隊成員平均 45 歲左右,有的都 55 歲以上。
事實上,出國并非互聯網人罕見的選擇。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知乎論壇發現,一位 32 歲的程序員問了一個問題“程序員年齡增大后的職業出路是什么?”,其中一個熱門的回答是去德國工作。后來答主表示,沒想到這帖子居然很受歡迎,因此收到很多私信,詢問關于如何來德工作和找工作的問題。
而在出國之外,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還留意到,不少在一線城市互聯網大廠打拼的互聯網“老兵”,有時候會選擇到其他一線或者二線城市工作,這些城市也有一些互聯網招聘不限年齡,但常常要求有互聯網頭部企業的工作經歷。
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認為,一些城市的生存競爭壓力更高,這時候不少互聯網人會選擇到其他城市去工作,比如一些深圳的互聯網人有時候會選擇來廣州。如果一個城市可以增加“互聯網+產業”的工作機會,加之提升醫療、教育的保障,就能吸引更多互聯網的人才來工作。
此外,轉行、創業或者兼職,也是互聯網人正在思考的轉型方向。比如趙軍目前嘗試做自媒體,給一些初學者和職場小白分享工作經驗,“雖然并不算成功,但我覺得也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另外,趙軍指出,資深程序員可以轉入培訓行業,給剛畢業的大學生或者在校大學生做一些業務培訓。“讓替下來的程序員在大學或職業學校里當老師,是非常理想的轉行,有不少朋友反饋說現在大學里很多老師都是空對空的理論教學,缺乏實踐經驗,教出來的學生也不能直接上手。”
汪程也做自媒體 3 年了,完成工作任務后,利用空閑時間分享知識和經驗,順便賺點錢。他有比較清晰的職業規劃,打算往更高層次的職位發展,不過也擔心遭遇晉升瓶頸,因此會思考給自己“留后路”,“比如創業開公司,長期的職場生涯沉淀了不少技術和人脈,可以跟朋友合作,或者自己出去找一些項目,有資源會比較容易。”
李強還提出了其他的發展方向,比如互聯網人可以寫博客,寫書,把自己多年積累的經驗和技能整理出來,有序的發表。這一方面可以擴充自己在該領域的影響力,也可以增加自己簡歷光環,為職業發展添磚加瓦。其次,他建議互聯網人應增加職業社交。
此外,他指出,得益于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智能終端以及網絡通信等技術的進步,為制造業、工業、金融、醫療、交通、零售、城市建設與管理、政府及事業單位等各行各業提供了突破性的新型科技產業形態,與此同時也增加了大量的新增崗位,而這些互聯網老兵,恰好有著更多的實戰經驗與之匹配,更有可能獲得更多轉行的機會。